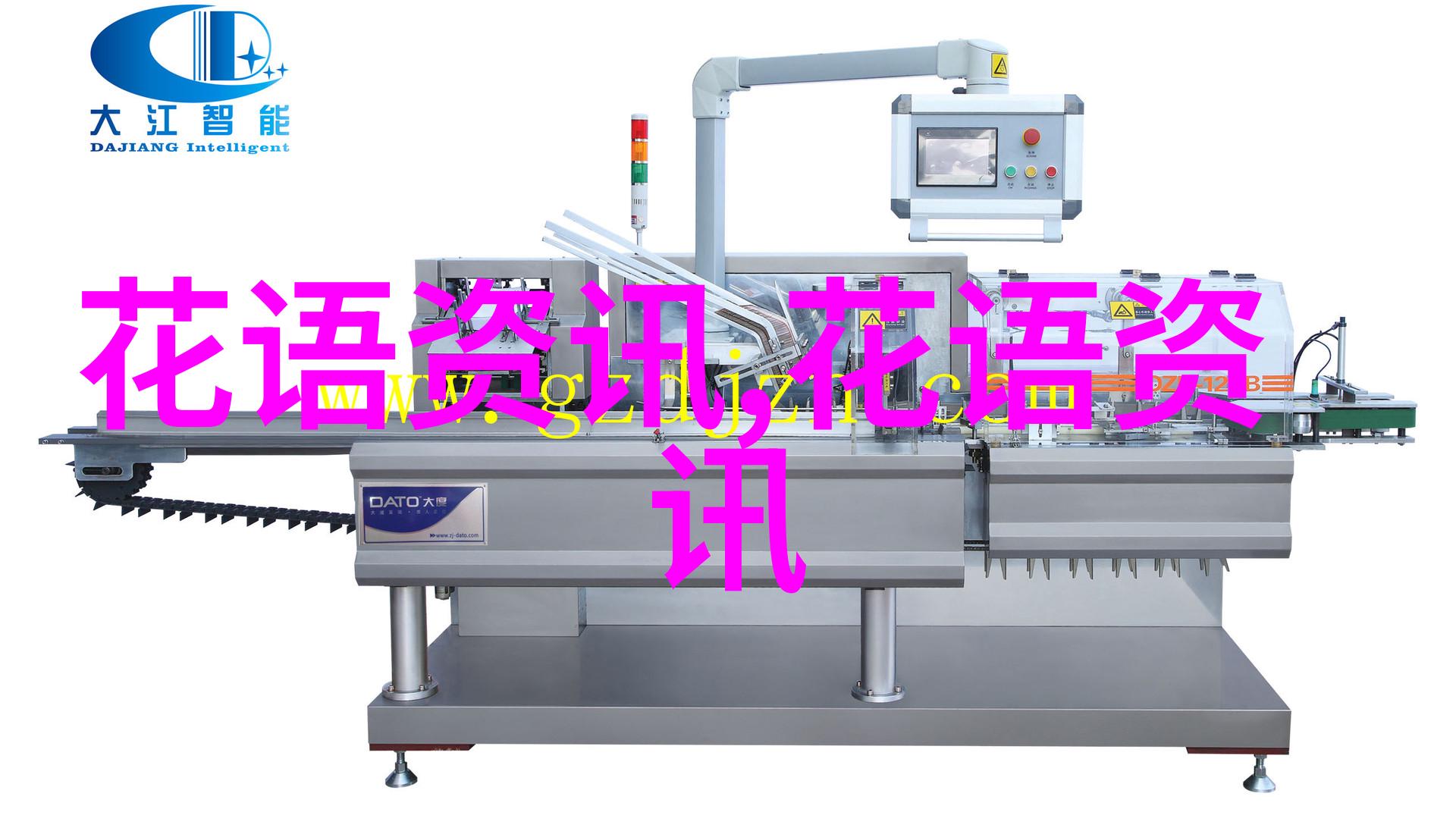栗:我们第一次见面,大概是你毕业创作展览的时候吧。 曾:对,91年的夏天,毕业创作刚刚做完,就是《协和医院》那组画,你看得的就是那个三联画。实际上我在这之前就画了很多医院的画。 栗:那时我正在做后89展览,我觉得画得很好。当时我也想找更年轻的人参加后89的展览,心里就有了谱,但你只有那个联画,想让你再画一些画。 曾: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清楚展览的事,但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,因为那时候魏光庆和曹丹对我说你很重要,说你可能要做什么展览,但他们没有给我说得很清楚。 栗:当时我看了你的《协和系列》,很吃惊,我觉得你的风格已经很成熟,现在十几年过去了,那些画还立得住。不像大多数的毕业生,毕业创作还不成模样。怎么会形成那样一种风格的?包括我在你工作室还看了一些没有展出的画,我看几幅像贝克曼的风格,你能谈谈它和《协和系列》的关系吗。 曾:应该是从大学三年级我的个人展览开始。我当时上课的时候是按照学校的课程安排去画模特,而课外喜欢用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去画。我喜欢画我身边的人,画我周围的朋友和街上的一些人,有时画些速写,拍些照片,但主要的还是肖像。那个时候特别想要表达自己的感觉,也画了一些抽象的东西。但最后我觉得画人物是我最感兴趣的,人物的那种情绪,看了以后特别有感觉。然后在画毕业创作了,觉得这样画一个个的单个人,参加毕业创作可能有点薄,可想来想去也想不好怎么画。那时我住的那个地方,离一个医院很近,每天因为借用医院的洗手间,所以经常要去那里,天天都看到医院那种排队候诊的情景,看到病人出事、抢救的情景,我忽然觉得,这就是我要画的那种感觉,我想应该画一组这样的感觉。就酝酿一个大一点的作品,我把我当时作个展已经有过的技术、技巧和观察方法都用上,画的过程特别兴奋,我感觉到这组画画好了,画完以后我特满意,第二天还没干,我就想拿到学校去给老师看。他们看了,我观察他们的表情,我感觉他们很震撼,但他们都没说什么,那个时候互相看作品都不大表示什么。我自己觉得特别喜欢。 栗:我想非常详细地知道,在此之前我看到的还很像表现主义,而到这儿完全是你自己的了,中间发生了什么特别的变化? 曾:刚开始我上大学的时候,确实喜欢很多表现主义的东西,很多大师的东西我都看了。我感觉我在学每一个人,比如说我也学杜菲,他的线特别好,画一个东西,他可以把这些线画出去再画进来,画一个人,这个人的色彩在里面,但线可以钩回来,我觉得他的线运用得特别好。同时我也特别喜欢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大师德库宁,他的用笔特别有力度,我很喜欢,但我觉得用这种方式画人的话,肯定难度很大。我当时也试过几次,还可以,但不成熟,我后来就连续地画了一些这样的东西,最后画《协和》的时候,在画手和头像时,找到一点感觉,最后一张我反着用笔,笔触往相反的方向走动,我要的感觉就出来了。 栗:你觉得《协和》这组画,和你刚才讲的,就是和你吸收的东西——你提到的那几个画家比,你把很激烈、神经质和狂放的东西一下子给压住了,处理得比较谨慎而且有点小心翼翼的,不象那么随便地画,这和你画的人有关系还是和你的性格有关系? 曾:我觉得和我的性格有关系,有些小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控制一下,我画人也是这样把握的,不像完全狂放得收不住边,但是我又要把那种感觉保持住,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。如果要完全放开,就彻底放开,我以前画过收不住那样的作品,完全半抽象的,看不见人的形状,但我始终就觉得这样没有太大的意思。你要想处理有点故事情节和特殊的人物造型,但又不能完全按照那样的造型去画,否则就没有太大意思。 栗:我觉得一个是和你的性格有关系,还有一个是你感触的东西其实是比较具体的,医院里面人的表情,医院里发生的事情给你的刺激,这是很重要的。这样你就找到了创作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,就是你对生活,从医院联想到人生很多相似的东西。 曾:是这样,这与我从小生长的环境确实有很大的关系,很多各种生病的人呀,还有各种残疾呀。因为我从出生到来北京之前,都是在那条街上长大的,那条街人的感觉实际上是印在我心里的。不管我以后怎样穿西装打领带,那都是些表面的感觉,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,给我一些触动,永远无法抹去。我肯定要表达、要发泄,或者说一定要释放出来,这实际上是一种情不自禁的感觉。那批东西都是在这样的状态中出来的。 栗:你中间还有一段画了一些肉。 曾:《协和医院》第一个系列完成以后,我就画了一些肉,开始是单独的肉,没有人,后来又把一些肉和人混在一起,人和肉躺在一起,肉在下面,人躺在上面。我比较满意的一张是《肉联之二》。我有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,对我很有触动,我们武汉夏天特别热,那时候不可能有空调,电扇一些地方有,但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,有一个卖肉的地方,那些肉都是从肉联厂运来的,整个是一个冰块,冰冻的肉,很多人就躺在上面睡觉,夏天的时候,在冰肉上睡午觉是很舒服的。我拍了一些照片,回来画了这张画。 栗:他们当时是乘凉的,但你画出来感觉很残酷。 曾:确实是这样的,我也一直在想,我为什么要这么画,后来我想可能是一些别的感触让我这样画,我觉得人的皮肤的颜色和肉的颜色,有的时候很像,还有一条腿出来,被什么东西压住,还有那些肉被砍掉的东西,都放在一起,我看的时候,就想到人的这种感觉。后来我也画了很多肉,我故意把那些肉的颜色和人的颜色画得一样,还用肉被压在一起的感觉画人。这些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,它使我后来我用的颜色在《协和医院》里有了改变,变成肉的颜色了。 栗:这个东西后来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。 曾:我画画的时候一直习惯用这种颜色。十几年我回头一看,一直在用这种颜色。 栗:包括你现在的生活,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是很不错了,但你还是在画这样的东西,是不是内心还是有这样的感觉。 曾:我觉得是这样的,现在生活确实是在物质上改变了很多,改变的越多,我就越是觉得有些东西是不能改变的,我内心的一些东西让我觉得改变不了。虽然物质上改变很多,我内心也还是有一些不安的感觉,有了孩子以后,我对这种东西越来越敏感。 栗:能具体讲吗? 曾:我也说不清楚,也没有一个具体的事情让我产生这种感觉。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一个人在物质上改变了,可我周围的人谁也没有改变,我的亲戚和朋友,我每年都回去看他们,我一个人的改变是我和他们有了距离,其实我想了很多,我想我这种改变是……怎么说呢, 栗:是虚假的, 曾:对,只是我个人的,一个人的帮助其实改变不了所有的事情。但有时侯你对一个人的帮助越多,相反越会给别人带来一种压力,别人那种感觉会特别痛苦。我周围的很多朋友,他们的生活还是老样子……我过去也画过一些很漂亮的东西,但我觉得那种东西都是舞台上的很虚假的东西,就是那种粉红的和黄的。 栗:是有蓝天白云背景的那些吧? 曾:是,我其实是想把它画得特别的灿烂,但特别的虚假,就像舞台上的一种布景。人都是一种自我安慰,等着谁来拍照的很做作的姿态,包括人的手,一种假装出来的得意的城里人的姿态,《面具》这批画就是这样的感觉。 栗:作为艺术家要保持人的基本良知,这是作艺术家的理由,你认为是吗。 曾:这是必需的,我觉得真的应该凭良心去做很多事情。 栗:这个阶段完了就是《面具》,《面具》有没有特别在生存上刺激你的理由? 曾:《面具》从1994年开始,当时我也同时在画肉这个类型的画,我93年已经到北京了,但这一年我还是在画武汉那种感觉的画。后来我觉得后期有几张画得不好,可能别人看不出来,可我自己觉得不好,有些东西感觉很熟练,但内心想得并不多,真正画内心的东西少了。当然技术更熟练了,全面了,我可以很好地控制这些东西,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。但我画画不喜欢仅仅是为了工作去完成这些东西,我还是希望在画的过程中得到一种快乐,不管这种快乐是发泄也好,是表达也好。说实话我后来发现我当时已经有点假装的感觉。我觉得这样走不下去,画得很失败。当然那时候我的造型一直在有些变,我平时也注意技巧,画医院和肉我偶尔也用刀,我想把这些技巧用来画一个戴面具的人,画大,看看感觉怎么样。我试了一下,想得并不多,但视觉效果不错,当时我的很多变化是因为强调视觉的感觉。 栗:“面具”有没有特别的生活上的感觉呢? 曾:“面具”我觉得可能是我到北京来了以后,刚开始真正可以交流的朋友其实很少,互相之间场面上的感觉太多,而且又需要和很多人去打交道,需要和很多人见面。我在武汉的时候就很少去交新朋友,也不会社交,都是很自然的从小长大的老朋友,到一个新的环境要学会和陌生人一起,这种感觉对我内心很触动,所以我觉得这批东西还是画了我自己内心的东西,不一定是别人内心的,只是我自己内心的感觉, 栗:你是不是感觉到人与人之间交往假面具太多, 曾:这是肯定的,有很多虚伪的东西在里面, 栗:从你到北京开始,我一直在旁边看你的画,有两个特点,一个是“面具”,比较容易看出来,符号性比较强,有象征呀,含义呀在里面,这个容易看。但我觉得你最重要的还不是面具,是你用刮刀处理过的,画完了以后整个一刮,就和以前的画不同了,有了新的表达方式——隐藏和修饰。后来有一段就是你刚才说的蓝天白云很像舞台化的东西,其实这些东西都和你想说的那些关于“面具”的东西有些相同的地方,但你又保留了一些比如最重要的“手”,你所有的东西都在变的时候,你保留了一个很痉挛状态的手没有发生变化。你处理这个刮刀的这种细节,技术上有没有这样的想法? 曾:对,是这样的。使用刮刀一方面也是想和过去有一点点区别,另一方面我想把一些强烈要表达的东西消除掉。用刀就是把过去使我特别兴奋的用笔消除掉,整个刮掉,让它保持一种平静,让那些东在里面。我不改变手的那种状态,是觉得有些东西你还是不能真正地改变。 栗:你所有的手夸张的大,还有粗大的骨节,痉挛状态。实际上我一直在看你,你一方面喜欢平时穿着讲究,但我有时候看到你性格上会突然不知所措,有一种痉挛的感觉。 曾:实际上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,场面越大,人越多,我就越紧张。 栗:《面具系列》一直到哪一年? 曾:应该到2001年,其实1999年,我就又画了一些抽象的,我对抽象的东西自始至终都特别感兴趣,我每次改变,都是从抽象的东西里体会很多,我从里面找到很多我想要的东西。我从1988年开始画抽象,上学的时候,当时整个状态都不对,觉得应该表达出来,就画了很多抽象画,很激动。现在我可以拿出很多早期的抽象的作品,都在我家里,一直到现在,我也画很多抽象的,不画具体的东西,不画生活中具体的情节,然后可以在视觉上改动。 栗:抽象是不是对你最近的这些画也有影响? 曾:对,现在画的都是我画抽象的时候感觉到的,把情不自禁的东西保留,然后放大,把一瞬间的小感觉放大,就是不断地找回到原来的位置上。抽象的画我也画,我可能自始至终都要画。也是我画别的东西紧张和压抑的时候,一个停顿一个休息。 栗:现在那种象螺旋一样的笔触,在画好了的画面上再画一遍,是从哪过来的?是在画抽象过程中的一个小东西的放大? 曾:是这样,我也是在画抽象的时候随意地画了这样一些东西,画白的和黑的,然后两个大的刷子刷上去以后,也是反着用的。后来我用一种小的笔触在上面随意地勾线的时候,把白的和黑的互相之间搅在一起,这种感觉让我一下子很激动,很有意思。这样的练习和制作,大大小小画了很多,我想往前走一步。刚开始没有太明确的东西,觉得有绞肉机把人的皮肤绞成这样的感觉,视觉上又有一种特别不安的一种感觉,内心的一种感觉还真是没办法用文字说清楚。我后来回头一看,我是几年还都是这样画下去的。上海这个个展我想起的名字是“我们”,或者是“有生命的冷冻场”,包括很多这样的东西在里面。 栗:我这次忽然看你这批绞碎的脸,我真的还是有点激 动,有点大师风范了(笑),我说的气派。以前你的风格非常完整,突然到这个阶段就有了一种气派,和以前的画比,气派大了。 曾:我这次去上海也是去完成一张画,各种型号的笔,有粗有细,每一种型号的笔都在上面使,就象中国人使用筷子吃东西,我的手特别灵活,我自己也尝试着顺着笔来画,怎么画你都看见是笔,不好看,我就反着画,这样上去,我自己觉得很惊讶,好看,挺有意思,不停地画…… 栗:什么颜色的? 曾:我一般都喜欢用单色,简单的颜色,黑的和白的,中间偶尔有一点点蓝色,很少的,白的地方已经画上去的后来又搅到底下去了,画多了,我觉得有点像勃洛克的那种感觉,但我觉得还是……刚才说控制,还是和他们有区别,但必须得一次完成。 栗:我觉得不像。因为勃洛克产生于达达时期,他强调的是一种无意识的偶然效果,而你的不是偶然的,实际上是完全控制的,包括你的你行笔呀。就是你的用笔折来折去的方式,让我联想到残荷败叶,秋冬的草,生命的挫折…… 曾:对对对, 栗:虽然用笔很连贯顺畅,但总是突然有折, 曾:对对对,这个折断的东西给我感觉很刺激,您观察的 特别细。我家种了一个紫藤,紫藤的枝就是这样的感觉,冬天的树枝突然的急转弯,断掉,突然地断掉, 栗:接下来还是和你的悲剧感有关系,可能是不自觉的。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折来折去的画面里有两道黄颜色,我马上想到干枯的植物……重叠,乱,但有很多折断的那个造型,是和其他抽象的顺着的笔触不一样。这可能和逆笔有关系,残荷衰草——逆笔——心情挫折是一种同构关系,会使人产生一种通感。 曾:以后反而这种东西更多一些,一层一层地压。我用白的黑的,就是不想有太多的过渡,我也画了很多其他的颜色,丰富的颜色反而没有这些简单的颜色效果好。 栗:你的画一下子又往上了一个台阶。我有时候担心你,你生活过好了,会不会在感觉上逐渐地变得对悲剧的东西不敏感,看来并不是这样。 曾:我如果画《面具》的话,真的可以无限地画下去,但我觉得这个就无聊了。此外还有很多东西触动我,比如在一些场合,别人介绍说他是什么,“他是面具画家”,就给我贴一个商标,贴多了以后,我觉得对我是一种打击,因为它已经变成一个符号了,我觉得不能这样长期下去。有几年我还挺得意,我的画大家都知道,细一想这不是一个好事情,这样走下去可能会没有意义。有小孩以后,对人生的东西想得特别多。一看到这个生命,就有很多担忧。未来是不知道的。我们小时候的生存环境和教育我觉得特别不好,你必须不停地想你是对还是错,包括我们上算术,让你算地主给你一亩地,你得到多少,他剥削你多少,我们就学这种东西。墙上的那些标语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”。作为一个学生你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。不知道你是否看过《一块银元》,里面有一个情节是喝水银把小孩给弄死。那个连环画画得特好,黑白的,但很惨,让人充满仇恨。 栗:我们都是在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,问题是你能不能,和有没有能力反省,能不能有独立的个人的立场和感觉。 曾:本来童年是应该充满阳光的。但我们所经历的教育过多的强调了阶级仇恨。你在这种阶级仇恨的环境生长大,获得的人和人的关系就不一样了。要么你什么都不想,你就傻瓜一个,你要想,要思考,想得越多越清醒,越不知道到底是你不对,还是别人不对。很容易把人弄得什么都不想,它让你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是什么样子,你真的不确定。我画了《最后的晚餐》,耶稣被出卖了,但所有的人都打了红领巾,而犹大打了一个金的领带,意思就是他放弃了最终的追求和理想。 栗:爱在艺术里是最重要的,因为爱才能使艺术家有人的基本良知,才能有基本的文化立场, 这个立场就是不屈服于主流文化和时尚,尤其时尚和主流文化勾结,它靠着媒体,铺天盖地,左右着人的神经。我看有些歌星和主持人,那种造作和拍马屁的样子,很恶心,也很可怜,那不是一个“人”呀,只是一个被主流文化异化的玩偶。人保持良知,有个人独立的意识和感觉并不容易,所以我觉得你始终清醒自己的感觉,清醒自己真实的生存环境,这和你一直把艺术当作释放灵魂郁结有关,这是关键。今年写春联,我有一个对子:艺术在灵府与宗教同质,作品于俗世和金钱共谋,横额:何去何从。我一向觉得艺术和宗教同质,都是把它当作一种灵魂自我拯救的途径。 “人人都是艺术家”是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命题,它的实质就是把艺术的权利放回在日常生活中,真正成为人的心灵拯救的途径,但是,另一方面,艺术体制所有的的层面、所有的环节,又都是在选择成功的艺术家,这和人人都是艺术家是一个悖论,这个悖论,对艺术家是个考验,你是看重名利,还是灵魂的自我拯救。